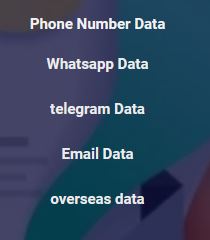在渊源理论方面,两位法官都明确区分(并“逐步”区分)了《欧洲人权公约》在规范性法案体系中相对于《宪法》的地位,而没有承认前者具有“准宪法”的效力,在我看来,这种效力是它应得的,因为其所处理的主题,尤其是其处理方式,使其具有对法律体系全部基本原则的强大“覆盖”。
德国法理学中的差距似乎更大,正如那样,它赋予《公约》与普通法相同的效力(“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Rechtsordnung stehen die Europä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und ihre Zusatzprotokolle – soweit sie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Kraft getreten sind – im Rang eines Bundesgesetzes ”:87),众所周知,这与我们法院的重建不同,其概念框架内部也相当复杂。事实上,一方面,《欧洲人权公约》被定性为“不合宪法”,同时又否认其与普通法具有同等的等级关系,并且同时又高于普通法;另一方面,它补充说,在它融入宪法参数的那一刻,它重复了后者的条件和等级,从而将自己定位为“宪法”的来源。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些波动实际上是由于从解释理论中获取的元素来源理论 美国电报号码数据 嫁接到理论主干上而造成的。
首先,法院告诉我们,问题在于看《欧洲人权公约》是否能够通过所有插入来源都必须经过的初步检验,即其是否与宪法规定相一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兼容性)。这可以通过应用某些解释技术来实现,其中包括希望严格化《公约》的解释,在各方面与斯特拉斯堡法院的解释保持一致(事实上,可以说很多)。一旦建立了这种一致性(或兼容性),尽管《欧洲人权公约》诞生于——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作为一个“亚宪法”来源,但它却成为(或被转化为)一个“宪法”来源,从而完全同化于后者,以至于在对涉嫌违反宪法的法律进行有效性判断时,被置于一个参数的位置。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