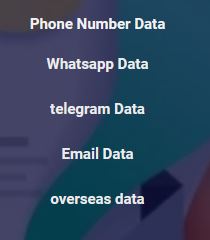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提交案件的法官并不掩饰他明显倾向于一种能够为案件法官保留适当的“自由裁量权”的解决方案,承认他“有权力和义务协助当事人制定初步问题” [14]。不过,他在以假设性术语提出问题时显得十分谨慎,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提出了双重替代性问题,一个问题“以上诉人当时表述的确切术语”提出,另一个问题则以同一位法官以实质性方式重新表述了该问题[15]。
即使在这方面——可以补充内容——人们可以理解(或者,也许更加谨慎地,似乎可以 巴拉圭电报号码数据 理解)“社区”偏见和宪法偏见之间的根本区别,众所周知,后者不允许提出“替代”问题,而评论中的裁决对这一区别的阐述是草率的,而且不够深入[16]。
事实上,初步裁定的具体原因在于解释的目的,以期在联盟领土内统一适用超国家法律;另一方则倾向于有效性判断,以维护宪法的完整性[17]。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第一种情况下,即使上诉至超国家的律法机构并非强制性的,也通常会受到欢迎,这与另一种情况不同,在另一种情况下,只有当其他旨在恢复系统和谐的工具被证明无效时,法律法官本人才会敦促普通法官向他上诉(众所周知,最重要的是顺从解释的技术)。
另一方面,[18]有声明称,除众所周知的(并且经常强调的)例外情况外,终审法官将案件提交联邦法院审理是强制性的,这种说法没有切中要点,而将案件提交宪法法院审理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表达了一种权力,在行使权力时要考虑事先对相关性的评估,而不是明显的毫无根据的。
因此,按照这里所描述的情况,似乎无论如何都必须消除可能违反联盟法律的风险,因为无论如何,违法行为本身都是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违反宪法的风险似乎会带来严重后果——我该怎么说呢? – 严重性较轻,最终留给普通法官自行评估,尽管违法行为本身 – 众所周知 – 是由法律造成的,因此即使在确定其无效之后,也无法消除其影响。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